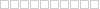411au勁舞團官方網站(http://www.chenxing369.com):那種暖和戛但是止
在這五年里,沒有一天不想念我的孩子。不論我如何努力讓本人忘卻,但總會在某一個不經意的時辰,某一個不經意的碰觸,讓我淚流滿面。
 我喜歡男孩,我不斷以為男孩比擬皮實比擬好養。我喜歡調皮頑皮的小男孩。
我喜歡男孩,我不斷以為男孩比擬皮實比擬好養。我喜歡調皮頑皮的小男孩。
我曉得我是一個小小的小女人。并為此而驕傲。
后來,我有了兒子。有了一個真正屬于本人的孩子。
我給兒子起了一個名字叫——臭臭。
有孩子的日子是快樂的,每個孩子給父母帶來的快樂都是無價的,都是永久和真實的。如今回想起和臭臭在一同的那段光陰,我依然能感到那一份從心底涌出的溫順。那是一種能讓鋼鐵消融的溫順。
還記得,剛出生時,臭臭是那樣的嬌小和丑陋。紅紅的皮膚皺皺的。像一個小老太太。我以至不敢碰他不敢抱他。他不停地哭。餓也哭,渴也哭,拉也哭,尿也哭。很長時間我才醒悟,他一切的表達方式也只要這些了。于是開端學習怎樣當一個合格的母親,初為人母的我仿佛忽然之間長大了,仿佛一下子有了義務了。由于這個小小的生命只要靠我才干存活,他只要在我的懷里才會感到平安,才會安靜地睡,才會中止哭泣。
我快樂的看著我的孩子,并真心腸感激上天賜予我這個如此美麗的小精靈。
隨著孩子一天天地長大,我覺察,原來我能夠這樣地溫順和寧靜,能夠這樣地慈祥和仁慈,能夠這樣地英勇和真誠。我的心中充溢了愛,讓我對每一個人都笑容。是的,我不停地發現著新的本人。
到如今我依然頑固地以為,一個女人假如不結婚會很不完好,假如不做母親就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女人。孩子會讓你的心異常柔軟。他那天使般的笑聲能夠洗濯塵世的一切污穢和懊惱,他那純真的眼睛會使你心靈如西藏的天空般地空靈和寧靜。當你抱著他的時分,當他小小的身體信任地依偎著你的時分,你會發現,在這個世界上你是如此地被人需求和不可短少。當他用純真的聲音喊你媽媽的時分,你會發現你真的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
漸漸地,他開端學走路。開端他在學步車里學習。他學得很快。常常看到他的身影在家里沖來撞去。他很獵奇,他看見鏡子里的本人會笑容,然后親一下,看見加濕器冒出的白煙也會伸手去抓。在我給他做飯的時分,他會把車停在廚房門口,獵奇地張望。他很依賴我,不管我在哪里,他都跟著。哪怕是我在洗澡和去衛生間,他都會重重地敲打著門,在確認我在里面的狀況下,安靜地等候我進來。
我如今仍分明地記得,那是1996年的春天,五月的微風溫順地吹拂著我綠色的短風衣。明麗的陽光暖和地照射著我,一切都暖洋洋的,我吸著芬芳的空氣,邁著輕快的步伐去接我的孩子。很忽然,就同被雷擊中了普通,我心中涌出來的幸福壓得我要窒息,那是一種暖暖的暗流,悄悄地流遍我的全身,直到達我的指間。以至,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膚每一個毛孔都覺得到了那種幸福。那一刻我問我本人:還有什么不滿足的呢?我有一個愛我的丈夫和心愛的兒子。我是多么地幸福。那是一種真逼真切的、扎扎實實的幸福。那一年我25歲,我兒子剛剛到一歲。
快樂的我啊,絲毫沒有發覺到災難就藏在我幸福的背后。它總是在你不經意的時辰降臨。
在他一歲三個月的一天夜里,他忽然哭鬧起來,我和愛人不斷哄著他,但他仍不停地哭,直到他哭累了,才睡去。第二天,他睜開眼睛的時分,左眼紅紅的。我抱他去醫院檢查,醫生只是通知我,點點消炎藥水就好了。于是,我給孩子按時點藥。但紅還是沒有消。快一個星期了,我又帶孩子去查。這次大夫仿佛很慌張的樣子。認真地查了又查。最后通知我,孩子的左眼可能會失明。而且,怕還有別的缺點。我驚呆了!一會兒醫生把我的愛人叫了進去,當愛人出來后,臉色慘白地通知我:“臭臭可能是眼癌!”我一下就呆住了:“眼癌?不可能!一定是錯了!”我抱著我的孩子走出醫院。我不置信。我的孩子安康生動,就算他的眼睛有問題了,也不可能是什么癌!我不置信!我要去北京復查!
第二天,我和愛人帶孩子去了北京。
結果終于出來了。
臭臭真的是視網膜母細胞瘤。真的是眼癌!
我一下子跌坐到了地上。很久才發現我已失聲痛哭。我的心中狂喊:“不可能!決不可能!”我感到血被抽干了,心被揉碎了。愛人讓爺爺把孩子先帶走,然后拉著我走出醫院,我們拉著手,漫無目的地穿越在北京喧嘩的人流中,淚水在我臉上猖獗地流著,我無法抑止本人的悲傷。我曉得茫茫人海沒有人能協助我的孩子,我也不能。醫生通知過:得這個病的孩子在走的時分兩只眼睛會都瞎的,而且隨著腫瘤的長大和游走,臉部要變形,會慘不忍睹的。想著孩子歡笑的臉,我不能置信這一切真的。他才一歲三個月啊,他的生命才剛剛開端,難道就要完畢嗎?這一切是真的嗎?醫生通知我,臭臭如今能夠化療,或許還有50%的希望,但是他必需停止眼球摘除手術,包括眼眶,化療的結果是這半邊臉永遠是他一歲時的臉,而那半邊臉卻正常生長。而且,即便手術勝利化療勝利也只能活到七八歲左右。我真的很想給他化療,當時我猖獗地抓著醫生的手一個勁地喊:“給他做手術!做手術!”但我也分明地曉得,這對才一歲多的孩子來講太痛苦了,更殘忍的是假如他活到了七歲,假如他懂事以后,他的痛苦也是不可想象的,由于他難逃一死啊!
那天晚上我和愛人作出了我們終身最難做的決議。我分明地記得在作出這個決議時我那剛強的愛人那張沒有血色的臉和悲傷的眼睛。我對我愛人狂喊:“不能夠!醫生說若不做手術,孩子會雙目失明的,最后雙眼會長出菜花一樣的東西,頭也要變形的,我該怎樣辦!當臭臭伸著雙手召喚我‘媽媽,媽媽,你在哪里?’時,我該怎樣辦啊?我會瘋的!做手術吧!不論結果怎樣,我們都不會懊悔的,就算是傾家蕩產,剜骨剔肉也要給他治啊!畢竟還有一絲的希望啊!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我的孩子死去!”面對著我的歇斯底里,我愛人,我心愛的人只是用力地抱著猖獗的我,向我吼道:“春兒,你蘇醒一點!你難道讓臭臭長到能夠質問你‘媽媽。我為什么不能活下來啊!’的時分嗎?你難道讓他就用一只眼睛來面對這個冷漠的事實嗎?你難道讓他飽受身體的摧殘還要面對那些獵奇的眼光嗎?”然后他用力地擦了一把眼淚。
孩子,原諒父母吧!我們是殘忍的,但也是無法的!我們必需這樣決議。我們寧愿讓你快快樂樂地活上一年,在你什么也不懂的時分走,也不要你受盡折磨才走。固然我曉得這個決議會讓我把內疚背負終身。
第二天晚上,我單獨背著我的臭臭,躲開了親人。我背著他走在午夜安靜的城市里,不斷走著,累了就休息,渴了就買瓶水。我不曉得要帶他去哪里,也不在乎去哪里。我只曉得我要背著他走,我要和他在一同。路上,我抱著我的臭臭問他:“臭臭,媽媽愛你,你曉得嗎?”臭臭通知我:“曉得。”我流著淚通知他:“臭臭,媽媽愛你,不論媽媽怎樣做,你要曉得媽媽是愛你的。”臭臭答復我:“曉得。”我問他:“臭臭,你來世還做我的兒子好嗎?”我的臭臭,什么話都會答的臭臭卻什么也沒說。我的淚水滴到了他的臉上。于是,我又換了話題問他:“臭臭,你愛我嗎?”他分明地答復:“愛。”
日子一天天地過,我還抱著一絲的夢想和希望。或許是誤診,或許會鈣化。或許這一切都是夢境。于是,我恐懼地開端一天天地察看我的孩子。他的左眼曾經失明了,但還看不出來,眼里只是紅紅的,后來就消了,但慢慢地原本是黑色的眼仁變成了灰色。在那一年里,我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看孩子的眼睛,我心驚膽戰地看著他睜開眼睛。假如,他向我笑容,假如,他洪亮地喊我媽媽,我的一天就會很輕松很高興地渡過。但更多的時分他總是皺著小小的眉頭,閉著眼睛賴在我的懷里通知我:“媽媽,我難受。”然后不停地翻轉他小小的身體。每當這時,我的心就緊縮在一同,我能做的只是抱著他,緊緊地抱著他。希望這樣能減少他的疼痛。希望能把他一切的疼痛都吸附到我的身上。我不停地通知他:“臭臭,媽媽在這里呢。不怕,媽媽在呢,媽媽抱著你呢。”然后讓他在我的淚水和歌聲中昏睡。我心碎啊,碎成了一片片,又被碾成粉末。每當這時,我總是痛苦地問本人:我們的決議對不對啊?我要救我的孩子啊。哪怕把我的眼睛和生命給他啊。我問蒼天:為什么!為什么要讓我的孩子忍耐這樣的折磨呢?為什么不讓他一下子死去!為什么讓他一點點地忍耐疼痛呢?我抱著我的兒子,抱著這個柔軟的小生命,這個依托我,難受時只會喊媽媽的小生命。我很懼怕,我怕本人總有一天會接受不了,我怕隨著他一天天地長大,他向我訴說他的覺得,我真的怕啊。我教會他很多的故事和詩歌,但我從不教他“疼”、“痛”和有關的字詞,所以,他臨走的時分仍只會通知我:“媽媽,我難受。”我曉得,只要我曉得這個難受的意義。那個難受里包含了幾不能忍耐的折磨!我的臭臭畢竟才一歲多啊!
還記得很久以前,有一則新聞:一個母親在本人走投無路的狀況下把孩子推到車輪下,然后自殺。新聞播出后是一片譴責那個母親的聲音。而我,能夠深深領會到那個母親的失望和痛,由于她已準備了死亡,她不能忍耐本人的孩子孤獨地生活在這個世上。
孩子的眼睛一天天地變化,變灰,變紅,再變灰。我恐懼地看著它在不停地變化。我不止一次地想象要殺死臭臭,好完畢病痛對他的折磨。我想象著給他打空氣針,吃安息藥,放煤氣,捂死他,或一家人痛快跳下樓。我每天騎著摩托車帶著臭臭穿越在車流不息的公路上,不止一次地想:要是有哪位好意的司機一下子把我們都撞死該多好啊。很屢次我都不得不停下車來穩定一下本人想撞車的心情。是的,我供認我是脆弱的。我無法忍耐他的痛苦和我的失望。
我的孩子活了958天,兩年7個月15天。
我的臭臭活著的時分,他出奇地靈巧,出奇地聰明,他和同齡的孩子一樣地心愛,不,以至更機靈。他會用不同的語氣來喊媽媽,來喊我的名字,他很會表達他的需求和感情,他會看眼色,會哄人。他很共同,很搶眼。不只是由于他留著童子頭,也不只是他有一根長長的小辮子。而是他很生動很有禮貌,他見到誰都稱謂。他喜歡小汽車,我給他買了近百輛大小不同的小汽車,每天他都不停地擺弄他的車。是的,我溺愛他,傾我一切來滿足他的愿望。看著他在不疼痛的時間認真地玩,對我是一種享用和幸福,我曉得我看的日子不會很多了。
在他病的日子里,我用了很多偏方給他治病。我帶他找過氣功巨匠,給他喝過他本人的尿液,給他吃蛤蟆的眼睛,去寺廟許愿等等。我曉得我很愚蠢,但是一切都沒有用。臭臭依然做了手術。由于他的眼睛里的東西已長大了,真的突出來了,他合不上眼睛。每次我幫他合眼睛的時分,看到他應該是眼球的中央已被一塊灰色的東西替代的時分,我都在哆嗦。我真的快解體了,我抓著愛人的手,狠狠地抓著,不能說話,但我愛人明白我眼里的猖獗。我曉得,再這樣下去,我會瘋的。或者,我當時在他人的眼里曾經瘋了。
臭臭被推進了手術室,他小小的身體躺在大大的床上,那么地薄弱和不幸。我望著手術室的門。我的生命似乎被抽干了。我向上天默默禱告:“讓我的臭臭不要活著下來,讓他死在手術臺上吧。”我真的是瘋了,世界上還有這樣的禱告詞嗎?但我當時就是那樣想的。我曉得,臭臭的眼睛將被挖掉。他那個眼睛的中央將是一個黑黑的窟窿。我懼怕,我不曉得我該怎樣面對他的痛苦。他即便做了手術也是要死的,不如在麻醉中安靜地沒有痛苦地死去。我哆嗦著。牙齒不停地打顫,身體不停地抖,止不住地抖。我的愛人拉著我的手,我們坐在手術室外的臺階上,遠離人群。緊緊地握著對方的手,那是我們唯一能抓住的中央。
手術車推了出來。我卻躺到了另一張床上。我很虛弱,從心里的虛弱。我支撐著起來。我必需起來,我是母親。我看到了他安靜的身體,小小的身體。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我抱起他,他是那么地輕盈,我抱緊他,我怕他飛走。他的左眼蒙著一塊大大的紗布。他的麻藥還在起著作用。他很安靜。那一刻我突然有個幻覺:是不是他死的時分也是這樣的?我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不要想啊。
臭臭瘋了,他猖獗地拉著他臉上的紗布。他疼啊。麻藥勁兒過去了。他掙扎著大叫:“媽媽,難受啊!媽媽啊!難受啊!”愛人用力地抓著他的手,一邊喊我:“春兒,快點,幫我抓住他!不要讓他把紗布拽掉!”我勉強站了起來,正在這時,臭臭掙扎著向我伸出了手并喊出了我終身中最難忘的一句話:“春兒!媽媽啊——!”那個聲音是那樣地蒼涼和無助,又是那樣地震動!
我終于解體了。我長這么大第一次暈倒了。
當我醒來時,臭臭已被打了安定針,昏睡過去了。
在醫院的日子是沒有記憶的日子,我如今依然想不起來。不曉得為什么,我如今只記得臭臭左眼睛上那一塊白的扎眼的紗布。
我曾嘗試過閉上我的左眼,想看看臭臭能看到的世界。當我看到后,我感到很悲痛。真的。
他常常用他那僅存的右眼信任地看著我,那是一只明澈如泉水般的眼睛。眼睛里流顯露的信任讓我悲傷。
我是脆弱的。我歷來就沒敢看我孩子那做完手術的左眼。我怕,我真的很怕。每次帶孩子去換藥的時分,我總是不敢進去。我躲到了眼科走廊。但我還是能聽到臭臭狂喊:“媽媽——媽媽——”的聲音。我躲到了電梯里,隨電梯上上下下,我用力捂住本人的耳朵,但臭臭的叫聲仍能聽到。那無法的喊媽媽的聲音飄蕩在醫院的每一個角落,揮之不去。是的,我逃不掉,永遠也逃不掉。每次,我抱著換完藥掙扎的沒力氣了的臭臭,抱起滿面淚痕但仍在嗚咽的臭臭,抱起向我撲過來讓我維護的臭臭的時分,我的心不是用一個“痛”字就能描繪的。
我問蒼天:這一切都是為什么啊?
蒼天無語。
在他做完手術后,醫生通知我臭臭還能活半年。我真的以為他能活半年呢,但只要兩個月,我的臭臭就走了。
臭臭要走了,我不曉得。我真的不曉得那是他要分開我的征兆。他不吃不喝,安靜地躺在我的懷里,輕飄得像一片羽毛,他小小的眉頭緊緊地皺著。我抱著他,只能緊緊地抱著他。而臭臭也只讓我抱著。他不停地在我的懷里扭動,不停地喊:“媽媽,難受。媽媽,難受。”我抱著他,只能緊緊地抱著他。
誰能救救我的孩子啊!
我把臭臭送到了醫院。在病房,我愛人去取住院的東西,我抱著我的孩子,抱著行將分開我的孩子,我哭了,沒有任何顧及地放聲哭了。我任淚水在我的臉上猖獗地流淌。我問臭臭:“為什么,為什么你要分開我!我是你的媽媽,可我為什么卻救不了你啊!”是的。悲痛的不是孩子有病,是我做媽媽的救不了孩子,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分開我,卻沒有任何方法。在空空的病房里,我無法的哭聲在回蕩。上蒼有靈啊!假如淚水能喚回我的臭臭,我寧愿讓我的淚流成海!假如用我的生命能救回我的孩子,我甘愿死一萬次!我的孩子,我的臭臭!只要他能聽得到我的召喚。但他已昏迷了。
臭臭走了。永遠地走了。真的走了。真的永遠地走了!我永遠記得那一天:1997年10月9日。我的靈魂被永遠地帶走了。
但我仍感激上蒼。他走的時分沒有像醫生預言的那樣,他的相貌沒怎樣變。固然他的臉有些細微的變形,但他的右眼沒有失明,他臨走的時分仍看得見我,他仍能精確地用他的小手緊緊地抓住我的手,他仍曉得他的媽媽在他的身邊——永遠!
我選擇了給他火葬。老人通知我,這樣小就夭折的孩子最好埋在路邊。我堅決不同意。臭臭在世的時分已飽受折磨,我不能容忍他小小的身體在冰冷的泥土中孤獨地睡去,不能想象他的身體受蟲蟻的損害。我怕他冷,怕他寂寞,怕他醒來哭喊著找媽媽。我要他化成輕煙,隨風散去。我要他干潔凈凈地來,干潔凈凈地走。
但火葬的時分我沒有去,我沒敢去。我無法面對我死去的孩子,我怕本人控制不了本人。我的愛人和我的同事去送的臭臭。回來后,我望著我的愛人默默地流淚。我的愛人啊,我剛強的丈夫,在孩子有病的時分他沒有哭過,但此刻,他在床上打著滾,用力抓著本人的胸膛,撕扯著衣服,放聲大哭。他只是不停地通知我:“春兒,我疼啊!我心疼啊!”我抱住他的頭,他虛弱得像一個嬰兒。他喃喃地通知我:“我看到臭臭被燒的情形了,那一刻,我真的想跳進爐子里去。”我抱著我的愛人,淚水不停地流。我只能通知他:“你真傻,你怎樣能去看呢?”愛人通知我:“我把臭臭的奶瓶放到了他的身邊,還有他的小玩具陪著他。我把他從冷柜里抱出來的時分,他那個樣子就像在睡覺,我親了親他的臉。我總覺得他馬上能睜開眼睛喊爸爸似的。我把他臉上的紗布摘了,我不要他在投胎的時分還帶著那塊可恨的紗布。”我的淚水滴在了愛人的臉上,我心疼啊,心疼我的愛人。這個剛強的男人!第一次流顯露他的脆弱,他對孩子的愛同樣是那樣地深沉。他不斷在支撐著我。在有些時分我能夠逃,但他不能。我能夠哭,但他不能。我能夠去述說,他不能。他只能去面對,只能選擇剛強。由于他是男人。在孩子病的時分,我把全部的精神都放在了孩子身上,疏忽了對愛人的關懷。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的同事通知我:“他上班時總是在那里發愣,或者一個人轉來轉去,像瘋了一樣。”我的愛人啊,讓我心疼的愛人啊,你不說,你什么也不說,你只是默默地單獨接受這一切……
晚上,我和愛人把臭臭一切的玩具、衣服和臭臭用過的東西,照片和我的日記,到十字路口全部燒掉了。
我悄然地留下了臭臭的一縷胎毛和一張他百天的照片。在那張照片上我有一張幸福的笑臉,快樂地擁抱著我的孩子。這是我留下的與臭臭的唯一的聯絡,也是我做過母親的唯一留念。再有,就是我對臭臭永遠的記憶和無盡的懷念。
我仍不記得那一夜我和愛人是怎樣熬過的了,那一夜我沒有記憶。
第二天上午。我把我的睡衣和愛人睡覺經常穿的背心剪了,在胸口那個中央剪的。我當心地把臭臭那少得不幸的骨灰包了起來。我希冀在冥冥之中臭臭能感到暖和,感到父母的呵護和體溫。但是,去埋藏孩子的時分,愛人仍沒讓我去,所以致今我仍不曉得我心愛的臭臭的墳在哪里。
我的孩子這一次真的走了,我今生今世也看不到他了,再也聽不到他洪亮的笑,再也聽不到他那特有的喊媽媽的聲音了。
除非在夢里。